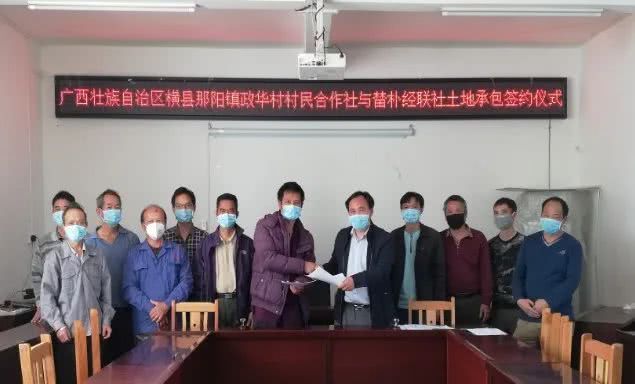“这场大火既展现了西昌干部群众的战斗力,也暴露出森林消防还有很多短板要补。”
撤离前,志愿队队长吉克三三拿手电朝山沟处的宁南队扫了几下,但没被注意到——志愿队和宁南队之间没有通讯手段。
“我们的指挥体系在目前条件下也只能这样了,指挥部远远地只能看到一条火线,对风向变化能稍早预警,但火场里地形和气候只有在一线才清楚。”
泸山近年来建设了不少储水设施,宁南队遇难的柳树桩区域,也有两个相邻的水库。但在3月30日当天,以水灭火的方法却没能在山上用上。

被烧毁的山火警示牌,依稀仍能看到字迹“草木有情,山火无情”。 (南方周末记者李玉楼/图)
2020年4月2日下午,柳树桩余烟缭绕,一片焦土。
这是一片位于两山之间的谷地,谷口朝南,坐落在凉山州首府西昌市郊。3月30日下午3点过,柳树桩西侧的马鞍山山梁上冒出滚滚浓烟,随后出现的火线北上东折,数小时内就将柳树桩围住。次日凌晨,前来驰援灭火的宁南县专业扑火队被山火包围,18名队员和1名向导牺牲,3名队员烧伤。
这场发生在“3·30”木里大火一周年之际的悲剧,再度将严峻的凉山森林消防形势推向公众视野。2019年的这一天,同在凉山州的木里县一场森林大火吞噬了31条生命,其中大部分为森林消防员。
西昌市政府人士向市领导转述幸存队员回忆时称,宁南队接到撤退电话后随即掉头,走了20分钟后在山坡上被大火包围,进退维谷。
这是19条生命悲壮的时刻蔡家沟在哪:队长命令队员全体趴在地面避险,把相对安全的位置留给年轻队员,一些队员则跳崖求生,22人中仅有3人幸存。
不同于2019年发生在原始森林的木里大火,2020年的泸山大火发生在西昌市郊,集结了全川消防力量和十余架灭火直升机,投入逾万人,可谓是凉山州消防资源最密集的区域。
4月4日,正在泸山视察的西昌市委书记李俊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场大火既展现了西昌干部群众的战斗力,也暴露出森林消防还有很多短板要补。”
次日,李俊在这次森林火灾反思暨后续工作会上说到,要加大护林防火基础短板建设,构建及时有效的应急救援体系,并提出五条反思意见。其中两条关于现场调度的分别是:反思当各方力量奔至时,是否做到从容衔接,不出纰漏?反思当应急协调指挥时,是否做到情况清楚,指令准确?
层层接应宁南队
30日晚上8点半,宁南县专业扑火队乘着大巴沿245国道出发,向120公里外的西昌行进,这条国道直抵泸山火场。司机邱师傅跟领导申请后,将大巴车时速上限由60公里上调至100公里。
在凉山州地方防火体系中,县一级的叫“专业扑火队”,乡镇则叫“半专业扑火队”,村一级为“义务扑火队”,前者在防火季的半年中全职驻训,后两者则是由民兵临时组成。
按照指示,这支队伍到西昌后服从当地安排,队长何贵银随队指挥作战,宁南县林草局办公室主任张明华负责协调和后勤保障。
南方周末记者获得的一份材料显示:出发时,张明华拨通了西昌市委常委刘光宇的电话,后者是泸山正面森林草原灭火前线指挥长。
刘光宇告诉张明华:“快到缸窑时再联系,往光福寺方向走,会有接应人员。”245国道在缸窑村伸出一条岔路,往北向光福寺方向是东线的泸山正面火场,向西则是南线火场。
晚10点半左右,西昌市泸山森林经营所(以下简称经营所)职工胡大成和护林员廖某在缸窑村接到了宁南队,带领宁南队往南线火场。经营所是西昌市林草局下属机构。
火情瞬息万变,当晚多支扑火队都曾在多条火线间调防。刘光宇此前表示,安排宁南队前往相应位置扑火是听取专家意见后的集体决定。
这一决定经由林业局、经营所传达至宁南队,直至宁南队上山后,仍需通过接应人、联络人、司机等这样一条纤细的联络线才能抵达终端,中间容不得一环断缺。
胡大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晚9点过,他接到经营所领导下达的任务,在缸窑接应扑火队。

遇难的宁南扑火队的上山起点。 (南方周末记者 李玉楼/图)
南线火场位于柳树桩和响水沟两个山谷,两地均属于西昌农垦有限责任公司下辖的大营农场,当地居民是从凉山各地自愿搬迁而来,不隶属于任何乡镇或村庄。
参与接应的廖某就是大营农场承包户,日常他也是当地的护林员,受经营所管理。因而在当晚协助接应扑火队,并帮胡大成记下了扑火队联络人的电话号码。
胡大成首先将宁南队带到大营农场场部,在此完成宁南队和农场方面的交接。当晚11点,宁南队抵达山谷内的蔡家沟水库,并遇见了农场安排的向导冯才勇。
据多名在场人士回忆,彼时火线已对柳树桩形成包抄之势,但东侧的火线还离得较远,而且是从半山腰往山上烧——山谷盛行南风,风向和地形看似都对扑火队有利。
预警辗转抵达
晚11:15左右,风渐小,宁南队从水库东侧山坡上山,农场组织的志愿扑火队跟在宁南队后面处理余火,负责宁南队后勤的张明华和司机邱师傅一起下山为队员准备物资。
与其他专业扑火队一样,宁南队上山时携带着风力灭火机和二号工具,后者也叫灭火扫把,即在木棍上绑上橡胶条,看似简陋,但在扑打小火时十分管用。
志愿队队长吉克三三回忆称,志愿队上山时,宁南队已经走到半山腰,隔着一段距离。当志愿队接近山顶时,宁南队已经进入山沟。南风转成了北风,东北侧的浓烟先于火线朝扑火队袭来。
风变大,火愈近。零点过不久,吉克三三在山顶接到农场打来的电话,要求撤离。撤离前,他拿手电朝山沟处的宁南队扫了几下,但没被注意到——志愿队和宁南队之间没有通讯手段。
随着志愿队飞奔下山,一直守在山下的廖某听到了队员们“撤退”“有危险”的吼声。
廖某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透露,他在零点二十三分拨通了张明华的电话,“就给说赶快下来,有点危险。也没人让我这么做,我是出于一个好心”。
司机邱师傅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当时张明华正在搬运物资,放在车上的手机响了,“我替他接通电话,廖大爷让队伍赶快撤下来,我立马电话通知队长何贵银撤退。何贵银慌忙中回复说正在撤退。”十分钟后,张明华再拨回去,电话就不通了。
西昌市政府人士向市领导转述幸存队员回忆时称,队伍接到撤退电话后随即掉头,走了20分钟后在山坡上被大火包围,进退维谷。
宁南队是在行进途中遇险的,多位扑火队长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在打火过程中,队长会站在靠后的位置观察指挥,还会在多点布设观察员蔡家沟在哪;但在行进过程中,队长通常会走在最前面探路,队员也较为集中,不会专设观察员,尤其在山沟行进时,对整体风向的把握会有滞后。
宁南扑火队的遇难地位于大营扑火队日常巡山的范围,大营队中队长朱拉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那个山沟里草丛很深,还有早年烧过的炭木堆积,火烧起来很快,不熟悉当地情况的扑火队很难找到避险区。
据界面新闻报道,身在大火一线的宁南队与前线指挥部并未建立直接的联系渠道。
4月5日,还在前线指挥部工作的马道街道办事处主任李恒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外地赶来的扑火队会留一个联络员在指挥部协调对接,大量沟通是在后方完成,再由联络人通知到各自的队伍。
当晚各方火线中,东西两线较为危急,灭火力量集中于扑救泸山正面山火和保护西线危化品设施,联防指挥部设于东线,前方指挥部设于火场西北,火势相对较小的南线尚未设指挥部。
据李恒军介绍,3月31日之后,前线指挥部就分东南西北几个区域设置,主要负责协调消防、扑火队和民兵的任务范围,为外地支援队伍介绍当地情况,配备向导。
“消防和扑火队都比我们专业,划定范围后,能不能扑、怎么扑肯定是由他们来决定。”李恒军说。
4月6日,指挥长刘光宇回应媒体称,国家、省级相关部门已组成核查组对19名扑火队员牺牲过程进行核查。
直扑火头的大营队
当日遇险的不只是宁南队。
不同于外来支援的宁南队,西昌本地的专业扑火队的对讲机都连通至西昌市林草局局长杨正平。建立于1987年的西昌市专业扑火队目前有8支队伍共260名队员,其中有6支分布在泸山四周,拱卫西昌之肺。
营地离起火点最近的大营扑火队最早冲入火场。

大营扑火队营地。 (南方周末记者 李玉楼/图)
30日下午4点,25名大营队队员利用两辆私家车、几辆摩托车和电瓶车驶抵柳树桩火场——这是一支没有配备机动工具的打火队。
“杨局长下达了直扑火头,阻断火势蔓延的命令。”大营队中队长朱拉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火头是指火线上蔓延速度最快、火势最旺的燃点。
回想起当天的经历,这名有21年扑火经验的队长还是有些后怕,当天他带领着大营队从柳树桩西侧的马鞍山北上东折。
“二十来个人实在打不下来,后方的火烧迹地又没处理干净,烟子熏得睁不开眼,眼见着要被火线合围,我们只好穿过火线跑到还没烧过的区域。”朱拉哈说。
当天的险情吓坏了不少大营队队员,朱拉哈事后跟队员总结说:“当天风向不稳,一下就跑到火头上去太冒险了,应该从火尾上打过去,把火烧迹地处理干净,这样就可以一直在安全区域打火。”
尽管打火经验丰富,但朱拉哈并不擅长同后方沟通。“局长怎么命令,我就怎么打,具体现场情况他也看不到,我也没空跟他讲,遇险时也只能随机应变保障队伍安全。”
类似的情况在多位扑火队长处得到印证。
马道队副大队长马永国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们的指挥体系在目前条件下也只能这样了,指挥部远远地只能看到一条火线,对风向变化能稍早预警,但火场里地形和气候只有在一线才清楚。”
曾在野战部队服役的马永国看来,专业扑火队只有配备了作战现场反馈装备,后方指挥才可能更有效,前后方也才能够在信息对等的情况下沟通,“毕竟火场里不可能花太多时间汇报火情”。
穿过火线后,大营队选择在距火线两个山头的山脊上开设隔离带。
凌晨1时许,南风转为北风,山头上的火线加速朝隔离带烧来,正是这阵诡异的北风,带走了宁南队19名队员。
当时,朱拉哈舍不得放弃这段刚开设了百余米长、二十米宽的隔离带——如果开设完成,就能保障泸山东南一线的安全。但派出的侦查员回报称,火头已经抵达离隔离带最近的山包下方,大营队只能仓促撤退,下到沟底的一处鱼塘附近避险。
下撤后不久,北风又转为南风,朱拉哈心生遗憾,“早知道就不用跑那么快了,还可以接着开挖隔离带。”但清晨得知宁南队遇难的消息后,朱拉哈既难过又庆幸,“谁也不知道北风会刮多久,继续挖还是太冒风险了。”
在陡坡上穿越火线
另一支接到堵火头命令的是太和扑火队。
3月30日晚,沿泸山山脊探路的开顺救援队队员曾兆阳缓慢接近火线,山脊两侧的火线都即将烧至山顶,由北向南蔓延。突然间,泸山正面的火场里冲出十几个人,这群人正是太和队的队员。
“他们劝我不要去,火太大了,他们自己的人还在火场里没冲出来。”曾兆阳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他当时非常担心,眼看着几十个人陆续从陡峭的火场冲出来的。
现有73人的太和队是西昌市专业扑火队的中坚力量,其中23人是2020年首次加入,一半以上有五年以上队龄。
中队长加多五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太和扑火队是西昌最早的专业扑火队,不同于其他7支队伍,太和队不承担巡山任务,专注扑火训练,是西昌市最为倚重的“灭火尖刀”。
3月30日泸山大火是太和队2020年以来参与的第11场救援。
当天,太和队是在战略放弃西线火情后赶到东线来的。加多五惹回忆,当他们上山时,天色已黑。他从对讲机中获悉,泸山正面和背面均有火线,且都是危险的上山火。
太和队负责泸山正面火场的阻击任务——把火头堵住,避免向南蔓延至光福寺所在的泸山景区。
为了尽快完成任务,加多五惹必须带领队员从距离火线最近的区域开路上山,在坡度超过60度的陡坡上穿过火线,迎击火头。
太和队的专业有目共睹,至少有4支与太和并肩作战的队伍向记者称赞该队扑火技术的高超:“跑得快,敢打大火”。
当南方周末记者将上述评价转述给加多五惹时,年过半百的彝族汉子腼腆地笑了笑,而后又皱眉说,“30号的情况真的很危险,零点过后风特别大,两侧的火都烧到了山脊,刚打灭正面的火头,又有背面的火星飞过来。”
当天晚上,太和队守住了泸山景区以北大片的山林,但其中一部分林子在4月1日晚间的复燃中被烧毁。
加多五惹和朱拉哈都感到惋惜,朱拉哈觉得如果那天凌晨把隔离带挖完,南线火就无法向东南蔓延,也不会烧去泸山。加多五惹则心疼冒死保下的林子最终没能留住。
30日晚的泸山正面火场聚集了五六支专业扑火队,半山腰上的山火朝上下两侧蔓延。装备较为充足的太和队能保证两人一个风力灭火机,因而承担了上山堵火头的重任。

西昌的马道扑火队的风力灭火机,只有6个可以使用。 (南方周末记者 李玉楼/图)
泸山队、马道队等队伍则死守下山火。
马道队三十余人只有六个能用的风力灭火机。“每年都会新配,劲也还行,但用二十分钟就会发烫,必须要撤下来。”马道队副大队长马永国介绍,扑火队的灭火机比消防员的落后不少。
此外,专业扑火队缺乏小型油锯、砍刀等开路工具。马永国说,他们用的是锄头、镰刀,遇到灌木就很费劲,如果装备配齐,开路速度可以很快。
除了灭火工具,多位扑火队队长都提到了防护头套、面罩的需求。“上回有个队员就是火星从领口掉进衣服里,给他烫安逸了(指烫得很厉害)。”马永国说,如果能有个消防员那样的头套就可以有效保护。
把水管铺上泸山
泸山近年来建设了不少储水设施,宁南队遇难的柳树桩区域,也有两个相邻的水库。
但在3月30日当天,以水灭火的方法却没能在山上用上。
30日西昌大火告急之时,凉山森林消防支队大部正在木里前线扑救一场28日烧起的大火,仅有一个完整中队驻留西昌,还要负责力保燃气站的安全。按照当天的部署,森林消防和消防救援队伍集中在几个液化气站和加油站,率先上山的专业扑火队则没有水泵和水带。
31日起,森林消防队带着水管、水泵发起总攻,消防员在东线火头上利用长达数公里的水带打开突破口,采取常规机具与水泵灭火相结合的方式,实现了对火场的迅速合围。

森林消防指战员在收拾水带。 (南方周末记者 李玉楼/图)
“‘3·30’那天晚上,如果我们有水泵的话很可能把火彻底灭掉。”马永国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天他的队伍在西昌农校背后的泸山扑打下山火,灭火机需要到一线的明火去扑打,而水泵则能够隔着几十米灭火。
两天后该区域复燃,十几辆消防车驻防在半山腰上的公路喷水。马永国坦言,配备水泵后对人员需求也就更大,背水袋、安水泵,至少得要1个班的人。他所在的马道队目前只有3个班。
4月4日,南方周末记者上山寻访扑火队员,途中遇到光福寺僧人在山梁土路更换生活水管,水管埋藏在土下五厘米左右。一位僧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一些是被大火烧坏,还有一些是扑火队员为了清理余火,刻意击穿,利用流水。“打火队没有水泵,只能背水上山浇灭余火,缺水的时候都舍不得喝,包在嘴里润一润口又喷向烟点。”
光福寺位于泸山正面山腰,仅光福寺蓄水池就储存了1000吨水,但由于水泵、水管、水带等基础配置欠缺,都无法在大火的第一夜加以利用。
西昌市林草局副局长骆弟东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该局早年做过测算,在泸山片区的山脊布设消防水管和抽水设施大约需要4亿-5亿元,由于财政吃紧以及森林区域建设审批障碍,一直未能立项。
过去十年,每次泸山大火都会促进当地改善消防基础设施:2012年的大火催生了3条山林防火通道,2014年大火后又新建了多个蓄水池,每次大火后也都会提出改善树种,配置监控等措施。
“下一步要沿山脊布设供水管道,既能植树造林,又能消防救火。”4月4日,西昌市委书记李俊站在烧毁后的泸山上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还要用彩色树种替换被烧毁的松树、桉树等易燃树种。
当天,山脚下的245国道人潮汹涌,沿途白花飘尽。接扑火英雄回家的18辆灵车驶回126公里外的宁南县城,这个只有18万人的小城沉浸在无尽的悲痛中。
南方周末记者 李玉楼 张笛扬 南方周末实习生 郑伊灵

1、IT大王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由于本站资源全部来源于网络程序/投稿,故资源量太大无法一一准确核实资源侵权的真实性;
2、出于传递信息之目的,故IT大王可能会误刊发损害或影响您的合法权益,请您积极与我们联系处理(所有内容不代表本站观点与立场);
3、因时间、精力有限,我们无法一一核实每一条消息的真实性,但我们会在发布之前尽最大努力来核实这些信息;
4、无论出于何种目的要求本站删除内容,您均需要提供根据国家版权局发布的示范格式
《要求删除或断开链接侵权网络内容的通知》:https://itdw.cn/ziliao/sfgs.pdf,
国家知识产权局《要求删除或断开链接侵权网络内容的通知》填写说明: http://www.ncac.gov.cn/chinacopyright/contents/12227/342400.shtml
未按照国家知识产权局格式通知一律不予处理;请按照此通知格式填写发至本站的邮箱 wl6@163.com